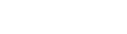这三个人,已不再贫困
樊专砚
题记:我是江西省修水县的一名帮扶干部,在帮助三个家庭战胜贫困的过程中,有很多感动和感悟。每一个贫困的家庭和个人都有隐秘而独特的精神世界,在此我掀开帷幕一角。
一
老刘一个人。
过去每次见到他,他就拉我聊天。主要是听他说,每次说的,基本意思都相似。上半段,他聊自己能力强、朋友多。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,就谋到了去乡政府做事的机会,后来还有去部队当兵的机会,只是因为父母反对都没有去成。他说他在广东打工的时候,与哪个地方的人在一起,就能说那个地方的方言。为了证明这一点,他会一口气模仿七八处方言给你听。他往往会在聊得最得意的时候,突然叹一口气,立即进入下半段,感慨自己的错。他说因为当兵没成,就离家出走,混迹车站当起了小偷扒手。他两个指头一伸,摆出剪刀样,作了一个掏别人口袋的动作,说,这样搞到的钱让自己越来越放肆。他说自己一九八三年他被判刑十五年,出狱后一无所有就继续一无所有,在广州游走于各小小帮派之间,只混个吃喝和痛快。近几年不想混了,他只得回老家安身。聊到最后他就会感慨,他说他这一生就是一个反面教材。
这些聊完了,他会聊点地理,武汉、广州的街街道道能说得身临其境。也会聊时政,对党的好政策十分认可。“小康路上,不让一人掉队”,事实上,他有切实的获得感。2015年他被评为贫困户。通过政策扶持,房子改造维修好了,养鸡养鸭养牛的致富产业得以发展,2018年就成功脱了贫。
但我觉得,老刘脱贫之后还存在的问题,就是太孤单了。他有一个儿子,小名叫“奉奉”。他初进监狱时,孩子的外公带孩子去探视过一次。老刘聊起这事几度哽咽。孩子当时两三岁,哭喊着:“爸爸,不要在这里,我们回家,我们回家。”此后,至今,父子俩都没有再次相见。奉奉随着远嫁的母亲去了安徽安庆生活。我曾按照老刘提供的线索帮忙打听过,想促成父子一聚,但缘分还没有成熟。这一点老刘理解,他自己觉得愧对,那边也年纪尚轻没有悟透。听说那边状况不太好,年近四十还未成家。这个话题,是老刘最柔软的部分,我们一般不谈。留待他们夜深人静、晨曦暮霭时刻去自己面对吧。老刘身体还好,冬天能坚持冷水浴,那一天,他应该能等得到。
走访中我发现,他与村里人关系不是真的很亲近。我想,这与他从事的一个营生也有关系。他一把快刀,给人杀猪宰羊,有着庖丁解牛般的刀法。刀子拿来拿去,联系他的过去,叫村民难免不“有所顾虑”。我私下与村干部聊过,不从事这个行业对他更好。很快,村里安排了公益性岗位给他——卫生环境监督员。
现在他很忙了,拉我聊天的劲小些。如果碰好闲下来,他更喜欢聊村里的变化,特别是卫生环境的变化。他说他每天早晚要在村里两次“检查”卫生,他的摩托车会洗得干干净净,龙头上还飘几条彩带。他说谁谁谁家门口不干净,他亲自帮他扫过几次,现在已经愿意自己动手了,成为村里最干净的地儿。他说很多村里人一看见他,就报告哪里的卫生好、哪里的卫生差。他说公益性岗位工资不够摩托车的油钱,但他不在乎,能为村里做点事他很开心。
有时去他家,如果见不到他,我就在门口看看他的菜园。
菜园只是四米左右长的三畦地,在四个角筑有钢筋水泥柱子,拉起铁丝网围着。这个小巧精致的园子,四季变幻而生机盎然。我每个月都要去看,每次都有不一样的美。有时泥土新翻的气息混合鸡鸭粪的肥味扑面而来。有时青翠一片与房子的白墙青瓦映衬得令人画意兴起。有时红的辣椒、紫的茄子、黄的南瓜争着跳入眼帘而你久久注目架上吊着的胖冬瓜,它青色正浓,绒毛娇嫩,叫你担心它会不会突然掉落。下一次你再来看,就会发现这个冬瓜被一个绳子编就的兜固定住了,成熟得通身布满白色的粉末。
有一次聊天,我对他说,这么多菜,可以找一个老伴来一起吃哦?
二
“我家三个人,有两个得了精神病。”
我的帮扶对象徐贺喜七十多岁,瘦瘦小小的,目光总回避与我对视。他方言味很重,嘀嘀咕咕的,不情愿也不善于与人交流,习惯于用笑脸表达。我第一次上门,听得最清楚了的,就是他这句话。
后来发现,这句话他说得这么溜,是因为他说得太多了,每次“村外”来人,他总要把这句话说一遍。怎么成了贫困户呢?他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解释,应该是他也需要一个理由!远看老徐家的房子,确实不像贫困人家,二层,砖混结构,外墙还贴上了洁白耀眼的瓷砖。走上他家的二楼,就能发现他家的困境之深。房间里的场景停留在过去某一天,到处灰尘很厚。“我儿子发病时,斧头乱砍。”每扇门、每张床、每套桌椅,甚至每个窗子都有斧头留下的累累砍痕,像老徐肘背上的刀疤陷在深深的皱纹里,鲜活但又沧桑。
老徐是一个外来户。他出生在樟树市,给流落到村里的一个樟树人作养子,才来到这里的。到他家,如果发现他不在家,我就在门口喊:“老徐——”。邻居们都会帮着喊:“贺喜叔公——,贺喜叔——、贺喜——”。感受得出来,大家对他很热情。有几次我看到他帮别人抱着婴孩。这些孩子长大了,该叫他“贺喜太叔公”吧!六十多年前,七八岁的他,小脚丈量了三百多里山路,跟着养父踏入这个陌生的地方,再也没有回去。六十年来,他一日一日奔忙在沙洲村的土地上,立足、成家、创业、和邻居亲如一家……。在他家的一楼,犁、耙、打谷机、风车等很多旧农具虽已弃用,但洗得干干净净,摆放整整齐齐。我仔细看看,把手和着脚的地方,都用得光滑而磨损,见证了他的勤劳和艰辛。印象最深刻的是,农具上都写有“贺喜”两个字。他没有署出“徐”姓,是有意淡化自己的外来人身份吧——村里只有他一户姓徐的。而“喜”字的写法,很是象形,草头下面一个口字,“口”却写得方中带圆,令人想起老徐的笑脸。
然而,命运之手把这个“口”字框全涂黑了。他儿子因为婚恋问题突发精神病,接着他妻子也发病。还有一个事,我没有跟老徐直说,他自己已经处于了肺癌晚期。2018年以来,他多次住院,我们骗他只是“肺气肿”的病。我去医院看望时,他还是那样,多是以笑脸对我。有一点变化我也感觉到了,那句解释性的话,他说得少了,更多的是感谢党委政府的话。也许身体的变化,已经促使他完全把身家和希望托付给党委政府了。这些年,他家的生活全部靠社会保障性托底,他儿子免费收治在县城的精神病医院,他妻子免费每天供药稳定住病情;仅2018年医疗报销,就免了八万多元负担。我也咨询过,如果有一天他走了,他妻子会安排到敬老院生活。我还特意去精神病医院,拍了段他儿子的视频:人很胖,表情呆滞但很红润。视频存在手机里,哪天他想看看,就及时给他看。
平时,他还是在家照料妻子;只有要住院了,他远嫁外省的女儿才回来照顾他几天。见他更加消瘦,我多次问他胸内痛不痛。我没有说出“肺”这个字。他总是摸摸胸部,摇摇头。有一天,我们顺路带他去镇上取药,在村部旁边的小超市门口,他要求车子停一下。我问他什么事,他笑而不答,只见他推开车门,急急忙忙往超市去,很快就出来了,左手捏着拿自超市柜台的红色塑料袋。返回车子时,他先是小跑了一段,风吹得袋子飘了起来。在一个垃圾桶里前面,他突然刹住,蹲了下去。他把红袋子衔在嘴里,把一直攥在右手心的黑塑料袋打开,把里面的低保证、贫困户证、医疗保障卡等东西全掏出来,放到铺在地上的黑袋子上面,接着开始揉红塑料袋的口子。他双手颤抖笨拙,好久没有揉开口子,手指几次放到嘴里舔些唾液后,红袋子终于开了。他把东西一一放进红袋子,包好攥在右手心,左手顺便捏起黑袋子团了团,丢进了垃圾桶。他一身轻松地到了车门前。上车后见我们心情沉重,他主动解释起来:去超市要了个红袋子,用红色的,喜庆吉祥些,这么重要的东西,用黑色的袋子装着不尊贵。
是啊,精准扶贫政策就是穷困群众的大红包
老徐的内心世界始终都是红色的。
三
“你知道帮扶干部的姓名吗?”
“是专樊见。昨天我们还见了面。”
糟了,荣大哥又把我卖了。我樊专砚的姓名总被他说错。我协助荣大哥与贫困战斗了一年,关系确实很亲近,但他一直叫我樊主任。要是问姓名,他就容易乱。出现这样的情况,我是理解的。他太忙了,智力忙得被人误会。听力也被人误会,他在做事,别人叫不应的。性格都被误会了,他很少与人聊天、交往,为一毛钱会争个面红耳赤。他摩托车骑得飞快,看着远远的,眨眼就到了跟前,沙沙沙一个急刹车。乡间小路错综复杂,风险确实很大,我经常提醒他注意安全,但他无法慢下来。
他智力残疾的女儿,在村里的小学就读。孩子与其他学生不搭调,动不动就跑出教室,冲出校门。荣大哥必须配合学校火速去找。
他大女儿读高中,15年出生的儿子患上肾综合症,家里的经济压力不堪重负。为了多挣点钱,他白天时间要去集镇打零工或山里砍柴,40多亩田地,上百只鸡鸭,他利用早起和晚归的时间打理。
荣大哥身材瘦小,是当地人说的“铁骨人”。有一个炎炎夏日,我特意中午去他家上户——他该在家里午休片刻吧——但他没有在家。返回的路上,我特意注意观察,终于看到了他。其实,我在来的时候,就应该发现他的。在我们往返的水泥马路上,他戴着草帽,身子弓成半圆,正在收起晾晒过的谷子。他手中的扫把像安在马力十足的机器上,快速扫动。灰尘弥漫中,变魔术一样,谷堆一个个在马路边出现。我们的车子慢慢靠近,我摇下玻璃,放出冷气和喊声。他直起来,衣服完全汗湿,一脸灰尘。我问他怎么中午就收起来。他说下午有事,也怕突然下雨临时收不完。把水泥马路当晒谷场已是当地习惯,再多的谷子马路也足够长。那天,我们的车子压过荣大哥的谷子,足足有十来分钟,但我们没有下车帮忙一分钟。现在想来,确实愧疚!
好在,现在荣大哥可以慢一点了。
他的残疾女儿,我们办好残疾证,送到县特殊教育学校读书去了,有专业的老师,有特殊的照顾。
他儿子的治疗,医疗报销在百分之九十以上,且先诊疗后付费,一站式服务。
他养鸡养鸭、农产品销售、技能培训,我们都为他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他还有了一套安置在城区的异地搬迁房,以后打零工就在家门口了。
其实,他是一个喜欢聊天,善于交往的人。怎么不是呢?他的妻子就是他外出务工时,娶自广东湛江的。前不久,我们聊了一次,把他差点聊哭了。我们远远看着他的儿子,那活泼可爱的样子叫人心底温暖,我突然对他说:“荣大哥,关于你儿子,你说过一句话,你自己可能忘记了,但我一直印在心上。”他惊讶地看着我。我接着说,你说过“我这孩子,得个癌症还好些!”。他呆住了,好久好久没有说话。我知道,他尽了很大努力,才忍住眼泪。
当时,孩子病情反复,两三个月就住一次院。多处咨询,又都说肾综合症很难治愈。打工聚的准备做房子的钱一分不剩,还欠亲戚朋友好多钱,已经举债无门。一家几口怎要活吧!他这句话里的绝望和悲痛,不结合当时的情境,确实难以理解。我听后当时一惊,慢慢才深入理解。艰难可以扭曲人性,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,我们必须战胜贫困。
我赶紧转移话题,说:“下半年,你儿子去哪里读幼儿园?”
他松开凝重的表情回答我。
“二女儿在特殊教育学校效果好,一家人都去城里哦!城里没有蚊虫叮咬,儿子病情复发的可能性更小些。”
我重重的点点头,是赞许、是欣慰、还是祝福……